【疫情哪年来的/疫情哪年来的?
“疫情是哪一年来的?”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在最近的家庭聚会、朋友闲聊中,竟常常引发片刻的沉默与犹疑,有人脱口而出“2019年底”,有人沉吟着说“好像是2020年初”,更有人模糊地以“就前几年”带过,那个曾经刻骨铭心、分秒煎熬的起点,正在日常的对话里,显露出第一道记忆的裂痕。
我们清晰地记得许多“感觉”——记得消毒水的气味如何霸道地侵占空气,记得口罩勒痕的隐约刺痛,记得屏幕里空荡街道的诡异寂静,但当我们试图为这场巨变钉下一个确切的时间坐标时,却发现它正在流沙般沉降,这不是遗忘,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位移:过于庞大的集体创伤,在试图纳入个人生命叙事时,产生了奇异的“时间褶皱”。
历史学者会指向一个个确凿的节点:2019年12月,首批病例报告;2020年1月,警报升级;世界卫生组织宣布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……这些是档案里的疫情,而我们记忆中的疫情,开端或许是自己取消的第一趟航班,是孩子突然开始的居家网课,是药店前第一次排起的长队。宏观历史与微观体验之间,存在一段充满张力的时差。 当国家层面的“抗疫纪事”与个人生活的“断裂瞬间”交汇,那个“元年”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年份,它成了公共事件与私人命运碰撞的模糊地带。

更深层地看,对起点的模糊,或许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,将一场持续数年、渗透至生活毛细血管的疫情,锚定在一个具体的“开端”,反而让它的庞大与绵长显得更加难以承受,模糊那个具体的年份,如同在心灵与一场浩劫之间,垫上一层薄薄的时间缓冲,我们并非不记得,而是记忆在以另一种方式工作:它更倾向于封装整体的“疫情时代”,而非尖锐的“爆发一刻”。
这引向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:当亲历者的记忆尚且开始波动,未来我们又将如何向后人讲述?史料记载骨骼,而记忆赋予血肉。 若骨骼清晰而血肉模糊,后世看到的将是一具怎样残缺的躯体?他们或许知道“2019-2022”的疫情时间线,但可能难以体会那种时间感——那些仿佛被按下暂停键又加速播放的日子,那些在方舱医院里从寒冬熬到炎夏的体感,那种不知终点在何处的漫长等待。

追问“疫情哪年来的”,其价值远不止于厘清一个日期,它是一次记忆的叩问,提醒我们:对抗时间侵蚀的,唯有持续而清醒的叙述。 我们需要在个人日记、家庭故事、社区口述中,保存那些鲜活的、带着体温和情绪的“时间感”,就像犹太裔学者对“大屠杀”的代际传递,不仅依靠历史书,更依靠无数个体的故事、诗歌、甚至沉默的传承。
站在今日回望,疫情或许正从“当代史”缓缓滑入“历史”的范畴,这个过渡阶段,正是记忆塑造的关键期,当我们谈论它的开端,我们不仅在确认一个事实,更是在选择以何种姿态,将这段集体记忆的接力棒传递下去。
下次当有人问起“疫情是哪一年来的”,在给出答案之后,或许我们可以多说一句:“那一年,我……” 因为最终定义那个时代的,不是冰冷的年份,而是无数个“我”如何度过、如何铭记、又如何带着伤痕与力量,走进年份之后的广阔光阴,时间的长河会冲刷掉许多细节,但人类通过故事,在河床上刻下自己的水位线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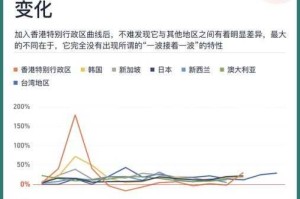
![[分析]“天王大厅有挂吗”有挂详细开挂教程 [分析]“天王大厅有挂吗”有挂详细开挂教程](https://blog.weiyanzm.cn/zb_users/cache/thumbs/65a88e0844f189599a57363a3f2379ad-300-200-1.jpg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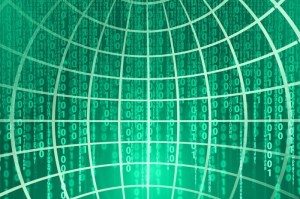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