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解除的时间是几点
凌晨三点,手机屏幕的光刺得人眼睛发酸,业主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“刚接到通知,小区封控马上解除,大家自由了!”后面跟着一串放鞭炮的表情,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,心脏怦怦直跳,是真的吗?我掐了自己一把,疼,窗外还是一片漆黑,但对面楼已经陆续亮起了灯,像沉睡的巨人忽然睁开了眼睛。
我抓起外套冲下楼,单元门上的封条已经不见了,铁链和锁堆在墙角,几个邻居站在晨雾里,彼此隔着口罩对视,眼神里都是不确定的试探。“真的解除了?”王阿姨小声问,手里还提着昨晚的垃圾袋,没人回答,保安从岗亭里探出头:“可以出去了,文件刚到的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我走向小区大门,那道伸缩门,过去三年里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,此刻完全敞开着,我站在门槛上——一边是小区的水泥地,一边是马路的人行道,这一步,我迈了三次才跨过去,脚踩在公共人行道上的瞬间,膝盖忽然发软,原来自由是有重量的。

街上开始有人了,便利店老板正在撕掉玻璃门上层层叠叠的二维码——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所码,胶很黏,他撕得很慢,像是在揭掉一块陈年的伤疤,早餐店的热气第一次在没有扫码枪监督的情况下飘了出来,油条的香味那么不真实,公交站台上,最早一班车的司机看着空荡荡的扫码机发愣:“…不用扫了?”乘客们面面相觑,还是习惯性地掏出了手机。
我走进地铁站,安检员拦住了我,我下意识地举起手机,他摇摇头:“不用了,从今天起。”过闸机时,我仍然把手机贴在感应区,那个熟悉的“嘀”声没有响起,闸机静静地敞开着,像一张沉默的嘴,我忽然有些失落——原来我们早已习惯被验证,习惯被允许,习惯在每一个入口交出自己的一部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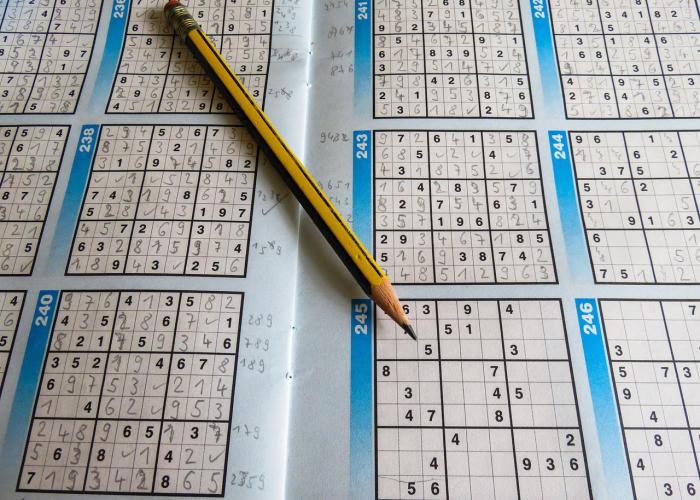
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,他什么也不做,只是看着湖面,我问他为什么不四处走走,他转过头,眼睛很亮:“我在等。”“等什么?”“等它真的结束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,“这里的闹钟,还没响。”
我忽然明白了,疫情解除的时间,从来不在任何一份文件里,不在午夜十二点,不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,它在母亲第一次放心地摘掉孩子的口罩时,在餐厅里陌生人重新拼桌的笑声里,在我们不再下意识地保持一米距离时,它在每一个重新学会信任的瞬间。
天完全亮了,城市开始喧嚣,车流声、鸣笛声、早市的叫卖声涌上来,像退潮三年后突然回归的海浪,我站在十字路口,红绿灯交替闪烁,绿灯亮起时,人群向前流动,没有人再小心翼翼地避开彼此的肩膀。
疫情解除的时间是几点?我的手机屏幕上,时间数字跳动着:07:46,但我知道,真正的答案不在任何钟表上,它在我们重新学会呼吸的这一刻,在勇气追上记忆的这一刻,在生活终于不再被“等疫情结束”这个状语从句修饰的——此时此刻。





![第一攻略.“十胡卡开挂辅助工具”[附开挂脚本详细步骤] 第一攻略.“十胡卡开挂辅助工具”[附开挂脚本详细步骤]](https://blog.weiyanzm.cn/zb_users/cache/thumbs/b6bd9a04a2eeb32a860b5970c89457b8-300-200-1.jpg)


![[揭秘]“陕西奇迹棋牌有开挂软件吗”[太坑了果然有挂] [揭秘]“陕西奇迹棋牌有开挂软件吗”[太坑了果然有挂]](https://blog.weiyanzm.cn/zb_users/cache/thumbs/04fd5c8d5a1689b463e8fcc899416070-300-200-1.jpg)
发表评论